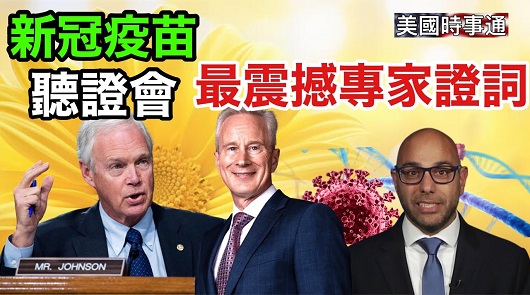「我在剩3個月的時候,盤算我能交代什麼事情,我發現,我在前面42年,我在爭的我在努力的,我什麼事都帶不走」
死過一次的人
41歲那年,江俊廷確診腮腺癌末期,惡性腫瘤像串葡萄躲在他胖胖的臉頰裡,壽命只剩3個月。當醫生變成病人,江俊廷選擇放棄治療,是父親要求他,不能輸給沒打過的仗。
3次化療再36次電療,他彷若行過地獄,再檢查,全身竟找不到癌細胞。
其實,他曾是個荒唐醫師,每週7天醉5天,打遊戲到深夜不睡。兒時為成績拚搏,大了在醫界爭鬥,他曾火爆痛罵院長,斥病人不遵醫囑。
如今,他總是呵呵笑,揹著包包就到鄉里人家造訪,只為確認病人是否乖乖休息。門診時跟病人聊生活談工作,從病人故事裡找疼痛的源頭。像是死過一場,他腳步仍快、心卻慢了,開始活得像個人。
第一次化療前,江俊廷寫了遺書,他記得自己邊寫邊哭,寫滿3張信紙。生命僅剩90天了,還能寫些什麼?死神在眼前急急敲門,最需要交代的仍是俗事,「我有多少財產啦,該怎麼分啦…但最擔心的還是爸媽,就跟弟弟說,我還剩下多少錢,請他幫我把爸媽照顧好。」
他想起當年還是菜鳥小醫師,看著神經外科總醫師像生死判官,召喚病人家屬前來,神色肅穆說:「這個某某人沒有辦法了,要有心理準備帶回去。」他也是這樣走進神經外科的,只是沒想到,這次死亡筆記本寫的是自己的名字。那年,他41歲,確診罕見的右側腮腺扁平上皮細胞癌,末期。
江俊廷上網查文獻,全球僅千例,活下來的寥寥可數。「我想查其他人怎麼死的,查不到。肺癌末期,可能是呼吸衰竭;腸癌末期,可能是消化器官衰竭。那我罕見癌末期,會怎麼死?不知道。」面對未知最是恐懼,他曾在夜裡崩潰痛哭,等死太可怕了,「我不知道我明天會不會死,也不知道我會怎麼死。」
但他活了下來。如今,江俊廷45歲,圓圓的臉龐帶著孩子似的稚氣,2顆大大的黑眼圈掛在眼睛上。是不是沒睡飽?他傻氣地呵呵笑:「這是遺傳。我們全家拍照時,像整家人都被揍,只有我媽不是…呵呵。」他吃素,身上沒有皮包與皮鞋,腰帶是塑膠的,錢包是個貓臉布包,盡量做到不殺生。
江俊廷是宜蘭羅東博愛醫院神經外科主治醫師,專長疼痛介入治療及神經外科手術。看診時,他習慣國台語交雜,語末的「喔」帶著土性,三、兩下就逗得病患哈哈大笑。70歲的阿嬤抱怨肩膀痛,他利索回嘴:「阿姨妳底厝偷搬金條喔!若無痛遐久…」阿嬤一巴掌拍上他肩,「黑白講,阮哪有金條啦!」臉上已燦笑如花。
他是話很多也愛聽話的醫生,醫院人員對我說,江俊廷門診最花時間,平均每個小時只看4到5個病人,還把病人來歷摸得一清二楚。我求證江俊廷,他呵呵笑,「我在做『話療』。今天坐在這邊,人家來結善緣,還能跟他收點錢(掛號費),天下哪有這麼好的事?我就好好結善緣,好好把話聽完,好好給人家意見。」
追問下去,他才說:「以前,我覺得醫是醫、病是病,所以我們是不同世界的人。病人來,我是幫他解決問題。如果他不願配合,我就會火大生氣。但現在,我花更多時間聽病人講話,很多病人講完故事,他的心情好了,痛也好了一半。疼痛不會突然發生,一定有來龍去脈。他講愈多,我就有更多資訊去找病因。」
打一場沒遺憾的仗
江俊廷的人生有個明確分野,是癌症畫下那條分際線。以前,他是白色巨塔裡的鬥雞。即使生活舒適、無肉不歡,又是受人敬重的醫師,但他仍不滿足,「我每天都在鬱卒,計較東計較西,計較薪水職位,為什麼升他不升我?為什麼我的車比較差?為什麼人家的房子比較好?」吃點虧吧!可不行,二倍討回來,還曾攔住院長痛罵。
2013年6月,那年他41歲,老天爺送上一份大禮。他罹患罕見腮腺癌,被宣判只剩90天壽命。
確診當下,江俊廷震驚之餘竟笑了出來,「欸,輪到我了,怎麼會輪到我了?」生命只剩3個月了,當醫生變成病人,他選擇放棄治療,打算預約安寧病房。父親得知後奔到門診找他,要他打一場沒有遺憾的仗。「爸爸說要給我一個任務,想辦法把我自己治好。我想,好吧。搞不好,這是爸爸給我的最後一個任務。」
江俊廷是長子也是長孫,從小他跟著阿嬤睡,阿公阿嬤期待他當個醫生。父母親都是老師,對孩子的教養極為嚴格,對長子尤其要求,期待他當弟妹的榜樣。國中時,江俊廷的成績還是全班前三名,高中考進台中一中後,佼佼者眾,他的成績直落到班上前30名。他只會讀書,卻也不會讀書了,內心開始感到自卑。
填大學志願時,他原本想讀控制工程,跟父親長談之後,在志願卡中加入醫科,心想當填心願的吧!只不過那是長輩的心願。後來,他吊車尾考上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。放榜那天,父親呆住了,要兒子不要誆他,接著獨自喝酒喝到醉茫茫,「爸爸太開心了。我跟他說,私校很貴,不然我重考?結果他說,免啦免啦,我拚給你讀。」
是父母最驕傲的兒子了,當上醫生、買了房子,人生看似往上坡走,迎接他的卻是癌症末期。像是重心倒下,全家都慌了,倒是他一派灑脫。弟弟江俊儀記得,自己考大學時,第一天考試結束,哥哥淋著雨騎單車到宿舍看他,只為送碗魚湯,看著他把魚湯喝完,叮嚀他早點睡,又在大雨中一路淋回去。
江俊儀說,哥哥看似愛「練肖話」,其實內心細膩。他考完高中聯考時,哥哥說要騎車載他兜風,2人騎了好長的路,「他邊聊邊說,高中了,要學會安排生活,想想未來要做什麼,像是把他的經驗傳給我。」像是一場哥哥的成年禮,同樣的情節也發生在妹妹江佩蓉身上,大學放榜後,江俊廷也載著妹妹兜風聊天。
或許真有長子情結,即使只長妹妹一歲、大弟弟4歲,江俊廷自我要求很高,像個被迫長大的孩子。從小,江俊廷就是擋風遮雨的大哥,對弟妹也不吝嗇。江俊儀回憶,當年他剛開始工作,在台北要付房租,「我沒有錢,打電話跟哥哥求助,他馬上轉帳4萬元給我。」後來才知道,當時江俊廷還是實習醫師,手頭並不寬裕,卻一聲不吭為弟弟想辦法。江佩蓉也說,直到今天,只要哥哥在,全家人出門吃飯都不用帶錢包。
我要活得像個人
罹癌了,即使已是癌末,江俊廷還是選擇當個能承擔的長子,接下父親的任務,就治療吧!但他一心認為自己會死,悄悄寫好遺書,交代弟弟,等他往生後,燒一燒把骨灰拋海,牌位墓碑都不要了,「留名字給人家掃墓幹嘛,比爸媽還早走,廢物一個。」昔日長庚教授李石增為他組醫療團隊,他住進台北弟弟家,高齡70歲的老父也北上照顧。
3次化療36次電療,他頭髮掉光、感官異常,夏天家人熱到吹冷氣,他蓋2條厚被仍發抖。他味覺失調,吃白粥是酸的、蔬菜湯是辣的,電療導致口腔黏膜潰爛,一杯水得喝上2個小時。好友劉建明記得:「他和父親面對面,中間隔著一杯水,他好渴,但一喝水,口腔就痛徹心扉。爸爸看著他,喝一小口、休息,再喝一小口、休息…」
朋友勸他插鼻胃管吧!畢竟是外科性格,他還是驕傲的公雞,怎麼都不願意,寧可口噴麻醉劑,趁麻痺的15分鐘裡,硬生生吞下食物。他體重暴減40公斤,身體極虛弱時,連從房間走到洗手間都沒辦法。父親勸他包尿布吧!他仍是硬漢一枚,整整6天,他爬著去小便。回想起當時,妹妹江佩蓉眼淚直掉,「2XL的衣服掛在他身上,他就像一片葉子輕飄飄的。」
在家人面前,那是江俊廷難得示弱的日子。有次電療完,江俊廷爬上弟弟位於4樓的住家,眼前一黑,就暈了過去。弟弟心有餘悸:「哥哥說,他當時覺得自己就要死在樓梯間了,我才意識到,我隨時都可能失去哥哥。」再有一次,妹妹北上看江俊廷,那時江俊廷剛電療完,2人並肩緩慢行走,江俊廷突然低聲說:「我很高興有人走在我身邊。」
療程結束時,他比預期的3個月,已多活了一個月。再次檢查時,奇蹟似的,癌細胞都不見了。罹癌7個月後,他燒掉抽屜裡的遺書,回到工作崗位。「我還活著,這是第二人生,我要活得像個人。」面對死神讓人謙卑,再看過去的拚鬥,他只覺得可笑,「計較了那麼多年,竟是忙著去死。」他戒菸、吃素,讀佛經、觀內心,生活漸漸緩慢純淨。
去年底,他離開工作近十年的台中慈濟醫院,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宜蘭。江俊廷在台中豐原出生長大,也等同離開自己的家鄉。為什麼?他說是為了吸一口好空氣,「最大的原因是環境,我的後半輩子想好好生活。那段時間,中部空氣不是很理想。」他總愛說,這是他的「第二輩子」,彷彿死過一次的人。
是個懂得活的人了。我們造訪江俊廷的宿舍,四周是稻田環繞,空氣極好。他獨居3房公寓,養了3隻貓。門也不鎖,說沒什麼好偷的,最貴的家具是貓咪跳台,5千元。他生活簡樸,相信身體與時序共轉,過餐不食,晚上多是煮飯燙青菜。唯獨薰香是小小享受,他收藏多種線香,還想開「京都尋香團」,帶隊買香。
天天聽自己的心跳
江俊廷過去是慈濟人醫會成員,常隨隊下鄉義診。轉職宜蘭後,常見老人家跋涉到市區看診,讓他再起義診念頭。南澳農夫蘇戴玉霞就是那條「導火線」,她深受下背痛折磨多年,一度痛苦到想喝農藥自殺。門診時,江俊廷仍是一貫練肖話風格,「我幫妳修理修理,如果還不好,我們再討論喝哪種農藥喔!」
得知蘇戴玉霞長年務農,他反覆提醒多休息,還撂下一句:「我會去看妳!」蘇戴玉霞不以為然,但還是畫下地圖。沒想到,江俊廷真的獨自造訪,當場被抓個正著,她又下田去了。想起那天,蘇戴玉霞好氣又好笑,「誰知道醫生真的會來!以前只有我們去看醫生,哪有醫生來看我們的啦!」下次醫師再來,她乖乖在家等候了,還帶著江俊廷在鄰里間四處問診。
我們跟著江俊廷穿梭在南澳碧候部落與朝陽社區中,一整天,他走訪了超過十個人家。其中一站是對老夫妻,2人加起來年紀近170歲,老先生長年腳麻,鎮日守著客廳椅子,怎麼都不願走路出門。80歲的太太天天煮飯,一路抖著手從廚房端飯到客廳,看著先生整日癱軟,老太太有天也抓狂,把稀飯摔了一地。
「上個月,我問他,阿北,起來走一走好不好?他給我的答案是,免啦,就這樣了啦!」這天再造訪,江俊廷在屋裡聊了半個小時,一句「你就為我走一下」,老先生終於起身,支著助行器,緩慢走出家門口。重新坐在家門口吹風,老先生瞇起眼睛,大家都笑了,太太叨唸著:「好幾年都不出來,都坐壞一張椅子啦!」
或許曾是病人,更能感同身受。江俊廷「探視」的目標不只病症,他耐心聽阿公、阿嬤說話,觀察住家環境、生活動線、支持系統等,生活的軌跡,都可能是疼痛來源。有阿嬤行動不便,只能坐床靠桌吃飯,他現場調整動線,避免疼痛惡化。就連冰箱他也不放過,邊聊邊參觀廚房,順道就打開冰箱,瞧瞧老人家都吃些什麼,還要檢視藥包是否重複。
大病一場後,江俊廷心慢但手快了,他說自己凡事不想再等。起初只有他一個人,無法現場治療給藥,他仍堅持每個月下鄉,他不怕一個人,也相信不會只有一個人。那天,2個醫院同事跟著去,眼明手快地記下每位長者的名字、年齡與狀況,準備回院討論後續治療。現在,院內正在籌組義診團隊,正如他曾說的:「邊走邊整隊,一定能走出一個隊伍。」
問江俊廷,還怕死嗎?他搖搖頭,不怕了。生命被宣判死刑時,他曾覺得可笑,這麼多年竟是忙著去死,引以為傲的那張專科醫師執照,死了也帶不走。在重啟的第二人生,他只求躺下去的時刻,心是安的。他不諱言仍有情緒起伏,但是每當心有不滿,他便自問:「這是我要的嗎?」不是,那便罷了吧,心也就開了。
剛當醫師的時候,江俊廷新買了聽診器,那時候天天聽自己的心跳,覺得有趣極了。罹癌的那段時間,他一次都沒聽過自己的心跳聲,就怕聽到死亡的訊號。採訪結束前,攝影記者請江俊廷用聽診器聽自己的心跳,在非常安靜的空間裡,他顯得有點震動,「好久好久沒聽自己的心跳了。現在聽到它,覺得…非常感動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