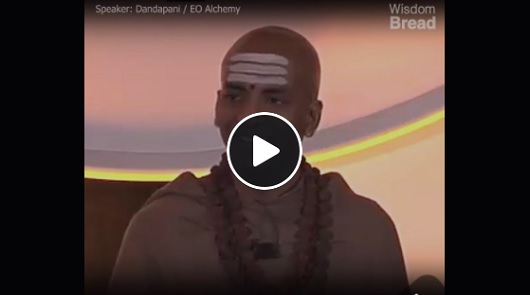「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,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。」
這是高中上補習班時,補習班老師高偉跟我們說的話。
開門見山,我的故事大概會是給不愛讀書的你、給想改變一些什麼的你、給半隻腳踏進大人世界,卻仍困惑這究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你。
我想試著用我半短不長、二十二年的歲月,講一個怎麼讓自己面對成長,逃跑得像在追逐,狼狽時還能笑出聲音的故事。
作者:張育萌
憑著國一的優異表現,我進了延平國中資優班
開頭適合來個浮濫的自我介紹,「我是誰?」這個巨大的問題,很難用我現在讀什麼、在做什麼來回答,但沒有過去那二十二年驕傲放縱又迷惑懦弱的我,也不可能有現在的我。
此刻,我是個台大社會學系四年級準備畢業的死大學生。
高中之前,人生大致沒什麼風雨,小學市長獎畢業,國中跟著姊姊去讀了延平。
延平是私校──我是需要人盯的孩子,從小放學就在安親班寫完功課才能回家,國中剃了平頭、繫上皮帶、衣服紮進褲頭,才能走進校門。
成長於台北市信義區的平房,我小時候是生詞簿只要沒有拿到「甲上上」就會有些失落的學生(現在回頭看,真想掐死高枕無憂的自己);國一學業總表現還拿了全學年度第八名,拿到了資優班的入場券。
逃離溫室:那班開往西區的夜車
這麼說起來,一隻腳踏進資優班的那一刻,改變了我接下來的人生。
延平的資優班是一個很詭異的地方,同學人都很好,善待彼此,彬彬有禮,如果台北市有個人口搜尋引擎,在搜尋條件選取「家庭收入小康」、「學業成績優異」,再按下「隨機」,這群資優班的同學就會一字排開出現在你面前。
雖然跟主題無關,但我印象很深刻。
一位同學問我偶像是誰,我不假思索說了「蘇打綠」,國中時候很愛裝文青,背蘇打綠的歌詞偷偷用在作文裡,就會被老師說把散文當新詩在寫。
結果那位同學說:「我也滿喜歡蘇打綠,但我的偶像是諸葛孔明。」他很崇拜他草船借箭的智謀。
在這個奇異的延平資優班異花園,我這朵花被放進溫室中的溫室,反而更加自滿,開始逃避書本。
從教室逃跑,躲進去的是西門町的撞球館。
從國三開始,每天晚上,我跑去7-ELEVEN買個便當,就騙爸媽今晚留在學校晚自習,然後跳上公車,往台北西區前進。
國高中時,我想逃離「完美的控制」
我總以為,是那時候的「學壞」,改變了我的人生進程。
從乖乖牌搖身一變,成為每天要去教師辦公室補考的問題學生;被老師盯上,我反而更想逃,我總覺得逃出學校,自己就自由了,從這個綿密的監視網絡逃走,逃到校園外的社會,到了西門町「瘋7」撞球館,高中生們叼著菸,制服換下卻仍背著書包,手握球竿,談些言不及義的話。
那是一種壓抑十幾年的宣泄,我國中時期很迷一部公視影集──《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》──
描述一位資優生在高中畢業前夕,面對家裡的債務、老師的懷疑、感情的猶疑以及背叛,終於讓自己的人生不再被「完美的控制」。
這位資優生叫作浩遠,國高中時,我總把自己投射在浩遠的角色身上,當時想逃離的是書本、考試,和天羅地網的監督控制;只是,現在回想,我大概對於被「完美控制」的生活有種天生的趨避能力──從小在升學主義中不斷斬獲,
立下一面面的旌旗,讓我在這條「資優」的道路上,看來再「合理」不過,但我總是想逃,並非是知識使我厭煩,而是我愈發厭倦閱讀那些我不感興趣而生硬的文字,最糟的是,我從來不知道如何面對自己對升學主義的反感,考試前我總會緊張得心悸,在考卷上寫下的每一個文字卻都是敷衍,敷衍對我有所期待的父母,敷衍好像沒有回頭路的人生。
「敷衍」與「不敢面對自己」是最可怕的,這一切會不斷地在人生循環,自己卻無法對任何他人言說,「不要管我」這種話變成藉口,向別人挑釁的說出時,也是在騙自己,告訴自己「我很好」,「是世界太爛」。
那天,經過自由廣場後,我開始投身社會運動
那天,一如往常,放學穿上便服,搭上開往西區的夜車。
台北市的街景萬年不變,雖然在這個古怪的城市裡,大多數的群眾都養成了見怪不怪的技能,但仍然,只要有任何一點差異就特別引人注意。
這天的自由廣場很不寧靜。
公車經過的瞬間,自由廣場聚集了零星的人,或喊著口號,或隨地坐下,頭綁著布條,談著我聽不懂的詞彙。
就像《女朋友男朋友》的劇情一樣,我帶著困惑下車,著了魔似的走進人群,聽著舞台上的人說喊。
我聽得出神,他說起了國家機器和資本如何控制媒體,讓媒體被個人或集團壟斷,讓這些看電視、看報紙的人成為有錢壞人實踐意識形態的傀儡群眾。
站在台上的男人叫作林飛帆,他在兩年之後衝進行政院,太陽花學潮爆發。
暫別街頭,好好生活
從跳上開往西區的夜車,變成搭著民主抗爭的社運列車,沒有想到人生會像量子力學般,完全沒有邏輯地劇烈轉折,卻也從此才切入正題。
那時候苗栗大埔有一戶要被迫拆遷,因為朋友拉著,我搭著末班的火車到現場聲援,十八歲未滿的毛頭小子,站在街頭上和警察拉扯衝撞,我試著用這些課堂外的流血流汗,更扎實地逃離升學主義的監視,也用最激烈的行動,來回應「我是誰?」這個問題。
愈是質疑,就愈是衝撞;然而愈是衝撞,就愈是想要挖掘真相,或是社會的答案。
但社會很冷漠,不論怎麼衝撞,怎麼探問,它不可能湊到你的耳邊,輕聲告訴你事實的真相,又或是我們究竟是誰。
我回到書裡找「我是誰」,於是進了補習班
那麼,「就回到書本裡吧!」
這個轉折很詭異,詭異得很現實,我想在知識中找到答案,回答「我是誰?」「我為什麼在這」,我想窮盡社會科學的知識,「我要考上台大社會系」,我這樣告訴自己。
這個科系目標,同時摻揉了世界對知識菁英必須考上台大才沒有「浪費台灣米」的盼望,以及我企盼成為一個獨立思考的人,真正不浪費台灣米的人。
振作起來奮發的契機是讀公民的快感,把我從街頭拉回書桌前,儘管重回知識的海洋,我仍戒慎恐懼,不論是對於久未謀面的學科知識近鄉情怯,或是在自然以及數學科不斷挫敗的沮喪,讓我在學測進逼的高三,踏進善導寺的一間數學補習班。
這間補習班很獵奇,坐落於民主進步黨黨部同一棟的大樓,上課的老師,是大家口耳相傳的「名師」,他叫作高偉。
我很痛恨補習,總認為那是升學主義下的畸形產物。
帶著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,踏進高偉,走上這趟學科的末班雲霄飛車。
我努力學習,如何面對痛恨的事物
高偉曾經說,他是要救那些身陷數學泥淖中的人,對,那個人就是我。
對於高中數學沒有及格過的我,我要學的是解題技巧,更重要的是,面對數學的態度。
這是高偉真正教給我的──我還是痛恨補習,但我們總得學會跟痛恨的事物相處。
在街頭衝習慣的我,也急於把看不順眼的一切,掃進歷史的塵埃,但我們總是不願正視自己的渺小,無法學著和厭惡的事物共存。
走了一遭,回到書海裡仍然是靠一份抽象的信仰,對於社會學的想望與熱愛,讓我必須全力以赴站上學測戰場,這時我必須了解,學習數學完全不是什麼興趣,就算我感到索然無味,也不能棄如雞肋──這時的數學,就像我們人生中所有想逃避的怪物一樣,是我們在奔向理想過程中,必須扛在肩上的責任。
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
如今的我仍離那個輕狂的少年不遠,享受社會科學的學院氣息,卻也由衷感謝曾經逃離教室,站在街頭,在沒有答案的考卷上努力書寫,試圖尋找線索的那段年少歲月。
結尾,我想用大一的導師陳東升的話來提醒自己,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。
「當開始懷疑那一刻,就註定不可能一帆風順,但仍然要相信,因為知識在一帆風順的時候,看起來總是很無用,但是,當我們迷惘無措時,我們能依賴的只有兩者──」他說,「知識,還有良知。」
改變是很漫長的,是一場馬拉松,我們看不到盡頭,這可能會使我們很挫折,像成長一樣,總是漫漫而無所依靠。
但我們都要知道,成長不是轟轟烈烈,實現理想的過程總有很多陳冗的事物,那便是我們人生的任務,讓我們學習如何不被現實耗盡,繼續記得我們的初衷是什麼。
「生活不能作為一種抵抗,」
東升老師說,「這樣太累了。」
「生活要作為一種志業,抵抗也是。」
在生活中抵抗,不論對象是自己,或是生活本身。
我們不能只想著要往哪走,要想著從哪來,一覺起來忘記自己受過的傷。
不要聽他們叫你「好好讀書」,
但要記得「好好生活」。